一元钱的变迁
迁安信息港消息: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元钱,曾经是家里俩人上学整个学期的费用总和,但还是有些孩子交不起。鸡蛋的价格,当时是3角钱左右一斤,5分钱一个,很多家长要赶到集市去卖鸡蛋,换了钱后,再给孩子交齐书费学费,有一个生动的说法类似今天所谓的“口红经济”,当时叫“鸡屁股银行”。为了这一元钱,孩子自己也绞尽脑汁想办法。力气大的,可以帮忙去搬砖,搬一百块砖赚一分钱,要很长时间才能攒够,记得张艺谋有一部电影,影片中孩子们去搬砖,给代课老师魏敏芝攒车费,差不多是一回事儿。力气小的,去山野挖药材,刨出红根,晒干,去药材店,药材店根据不同成色议价收购。刨一个秋天药材,也能赚一两元钱。我们几个小孩子则常去抓一种能入药的盖儿虫,挖时却常常捅出蛇来,吓得魂飞魄散,一直到跑回家门,心还狂跳。能入药的这种盖儿虫很值钱,八毛钱一斤,那时没见过金子,感觉金子也无非如此,所以挖起来很上瘾,冒了险也去,只要抓到一斤,就解了父母的忧愁,可以无忧地进学校读书,无论如何都要挖下去。成人以后,终于知道这种盖儿虫叫土鳖,在当时的我们眼里,每个土鳖都值半分钱。而一分钱可以买一块糖、一支笔,两分钱可以买到铅笔刀,七分钱能买到最好的连环画。曾经的小小盖儿虫,曾经的财富理想:挣够一元钱。
八十年代流行语是“一分钱憋倒英雄汉”,足见一元一角的厉害。有一个早晨,父亲照例给了一角钱去饭店吃面条。柜台服务员说,面条一角二分钱了,没有八分的价钱了,没办法,只好买了两个馒头。还有一次母亲备好一沓子五张一元的钞票,后觉得不好看,换成了五元一整张,给我未来的嫂子。给未过门的媳妇通常是三元,对媳妇只是说买双袜子,其实是买衣服用,说买袜子是客套,有点谦虚遮丑的感觉。母亲把一元钱换成了一整张崭新的五元,塞到嫂子手里,哥嫂在闹别扭,钱竟然被风刮丢了。母亲为此难过了很久。我在想,要都是一元的,刮跑了也会落下两张吧。
九十年代,一元钱的功用突然空前强大起来。一元钱的羊肉串、糖葫芦、冰棍、一碗满满的面条。上班没几年,工资涨到五六百,一年能挣好几千。这段时间里,一元钱不再是纯粹的面值,渐渐充当了找零的角色。在校小孩子捐款,很多捐到五角一元。汶川地震时学校组织捐款,很多孩子捐一百元,不留姓名,有的等不及就用短信把捐款发送给慈善机构,小学生没有捐助一元的,孩子们嫌丢人。今天的一元钱或许只能是超市的宠儿,留作找零。
一元钱,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复苏,见证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。
编辑: 周东月
 关闭
关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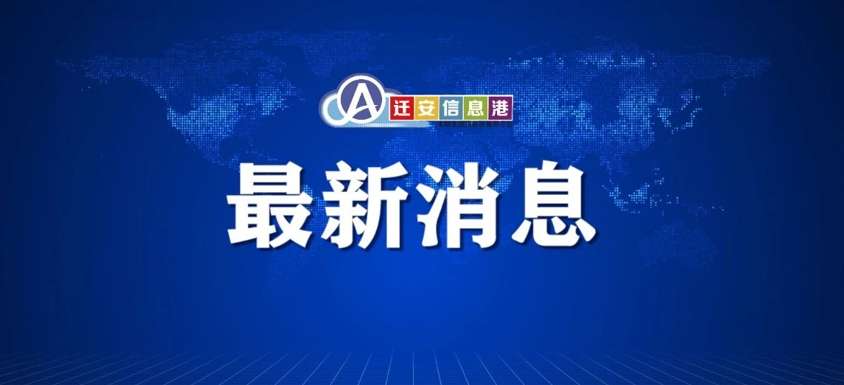
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