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缝纫机
母亲的房间里有一台缝纫机,蝴蝶牌的,机器脚踏板上的防锈漆已磨得所剩无几,这台缝纫机年龄几乎和我一样大,儿时的夜晚我是经常伴着缝纫机转动的“咔咔”声入眠的。如今,尽管多年闲置不用,母亲仍舍不得把它搬出去,而是精心地用一块红绒布把它罩了起来,闲时还经常用软布擦拭一番。缝纫机、彩电、空调,在母亲的房间里,这三大件被我戏称为“老中青三结合”,我多次劝母亲把这台缝纫机搬走或卖掉,母亲总是笑骂我“忘了本,要没这台缝纫机,你就得光屁股长大了”。
的确,我们一家人的缝缝补补全靠这台当时整条街惟一的一台缝纫机。快过年了,除了盼着一顿丰盛的年饭外,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一套新衣服了。于是就趴在炕沿上,盯着母亲把一块块布料裁好,然后打开缝纫机忙碌,那时听着缝纫机单调的“咔咔”声,是那样的轻快,那样的悦耳,“做好 ”,连熨都来不及,就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,跑到街上在小朋友中显摆一番。
那时候是计划经济,单是弄到一张购买缝纫机的票就费了不少事儿,而且花光了家里几年的积蓄,当时父亲把缝纫机拉回家,整条街的妇女都眼馋得不得了,纷纷围过来看稀奇,母亲兴奋得告诉大家:“大伙儿以后有缝纫活儿都拿过来,机器买来就是用的,不是当摆设的。”从此,我们家就热闹起来,每天都有几位家庭妇女拿来旧衣服让母亲缝补,但很少有人平时买块新布料做衣服,除非是快过年的时候,那时家里更热闹了,许多人围在母亲身旁看她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,家里的炕上堆了小山一样的布料,母亲忙得脸通红也不肯歇一会儿,有时一直要忙到深夜,她说,过年了,谁家都想做身新衣服,走亲戚时才有面子啊。平时,母亲用这台缝纫机帮左邻右舍缝缝补补,有时耽误了农活儿,大家过意不去,除草,轧碾,剥花生种,搓玉米,都主动为我们家帮忙,小小缝纫机,成了我家与邻居和谐相处的重要纽带。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富裕起来的乡亲很少自家做衣服了,母亲慨叹,咱家的缝纫机基本“退休”了。一次,一个收废品的老头儿相中了这台缝纫机,非要花50元钱买走,母亲的头摇得像拨浪鼓,不卖,不卖,没准还能派上啥用场呢!嘿,还真让母亲说中了,前几天,母亲和村里的几位老姐妹成立了一个秧歌队,老人家忙碌了一周,用这台缝纫机为大家做了10余套服装,我想,这没准儿就是这台缝纫机最后一项光荣的使命啦。(迁安信息港报道)
编辑: 孟令然
 关闭
关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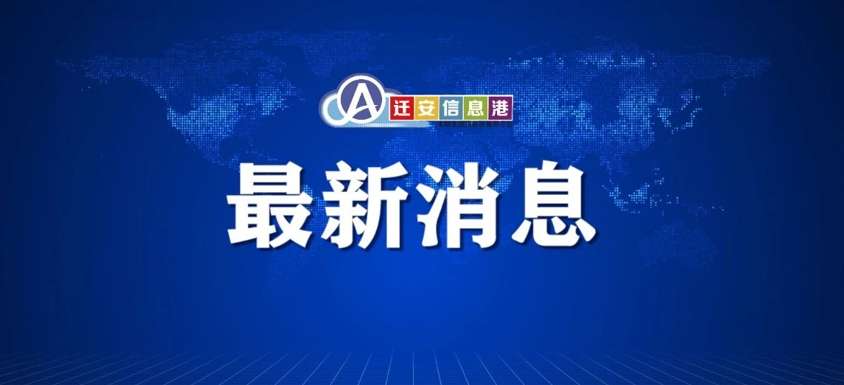

评论